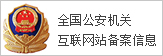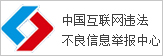16
姑嫂二人昼伏夜行,又行了两夜。按行程,早该见着盐池了,不料,却进入了一片戈壁。一见那戈壁,兰兰暗叫坏事了。记得那时,她去盐池,并没见着这戈壁,说明她们走岔了。那点儿馍已吃光了,水也只剩下一点了。清油虽没动,但就这点儿清油,熬不了多久的。驼的伤口虽已结痂,两人却不忍心再骑它。累极了,就一人牵骆驼,一人扯了骆驼尾巴,就能借些力。腿早不像是自己的了。后来,她们就轮换着骑骆驼,一人骑一个时辰。
驼峰已塌了下来,说明骆驼的生命贮备也不多了。途中有草的地方不多,虽然兰兰尽量选有草处昼伏,叫骆驼补充些营养,但驼峰仍然塌了。记得爹说,驼峰虽能贮存营养,但那是供万不得已时消耗的。要尽量叫骆驼水足草饱,尤其是水,最少不得。记得以前去盐池的道上,有几处地方,是专门为骆驼补充水草的。因迷了路,骆驼显然在吃食上吃了亏。兰兰就卸下驮架,从鞍子里抽出垫草,叫骆驼吃。然后,将自家的被子当了垫子。但那点儿草,对于饥饿的骆驼,仍是杯水车薪。
骆驼喜欢吃夜草,但夜里也正是赶路的好时候。白天虽也能吃草,但每到她们昼伏时,沙洼也成了蒸笼,骆驼吃上一阵,就经不了晒,卧入坑里。再说,也不是每次的昼伏,都能“伏”在有沙秸处。……驼峰不塌也由不了它。
好在那伤口倒长得快。这也是天性吧。因为老驮东西,驼背老被磨烂。久了,就结成了很硬很厚的老茧。盐一洗,伤口很快就结痂了。这样,只要骆驼有体力,就能驮她们。
不找麻岗时,会时不时碰到麻岗。那儿有嫩草,无论人和驼,嚼一点,当然没坏处。可你想麻岗时,它却连个影子也不见。某天中午,莹儿终于发现了一处麻岗,那儿有水有牲口,可兰兰说那不是麻岗,是魔鬼城。果然,不一会儿,那些美好的景致就变成蒸气了。要是去撵它,会跟苍蝇撵屁一样。
兰兰拧眉想呀算呀,终于认定,她们错过了盐池。她说,肯定是的。那盐池,其实是沙漠里的一块绿州,并不太大,你只要在远方错上一里半里,就可能跟它交臂而过。
咋办?
兰兰说,只好往回走了,等进了沙漠,再往西走。要是运气好的话,不定就能跟盐池碰个响头的。
再进了沙漠,两人将驼拴在柴棵上,上了一座看起来最高的沙山。上沙山虽然费力,但站得高,看得远,说不定你一上去,就会看到那白晃晃的盐池的。两人拖着比灌了铅更重的腿,几步一缓地上了沙山。她们用了至少两个小时,两人都累瘫了。喘了好一阵气,她们才四面搜寻。原以为这沙山最高,一登上,就会一览众山小的。不料,一上来,才发现,一山更比一山高。真没治。她们只能望见一浪浪啸卷而去的沙山。别说走,只瞭一眼,就魂飞魄散了。
莹儿叫,我的妈呀。她一屁股坐在沙上,半天不想说一句话。
兰兰也沉了脸无语。两人欲哭无泪,脑中一片空白。哪怕能看到天边有一片白——那是盐池独有的颜色——她们也会爬向那儿,可是天边仍是沙山。这算她们爬到天边,那儿有没有盐池,仍是说不清的事。
兰兰说,下吧。
莹儿说,我实在不想动了。索性,就死在沙山上算了,变成一堆骨头。
兰兰说,走吧,该走的路走过了,再说。
望着山下黄点似的骆驼,莹儿想,早知这样,上沙山干啥?既费了好多体力,也弄得心灰意冷了。
既然走不动了,莹儿也懒得再沿缓坡下走,她索性走到陡坡处,一蹲,坐在沙上,滑了下去。不料,那一滑,竟像长了翅膀,耳旁风呼呼着,身心一下子轻快了。到了一个缓洼,她听得兰兰喊,你小心裤子,要是再溜,你屁股上肯定会磨出个大洞。
虽也心疼裤子,但那感觉实在太妙。莹儿想,这乎儿,命都不知在哪儿悬着呢,管啥裤子?就跳下沙坡。沙流如水,载了她,感觉爽极了。许久了,还没这么轻松呢。她兴奋地叫着。沉寂的沙洼顿时鲜活了。兰兰也被感染了,她也不管啥裤子不裤子了,也坐在沙上溜下。两人都兴奋地叫着,把几天来的沉闷叫没了。
滑了一阵,莹儿怕屁股着沙处真叫沙磨破了。这是可能的。要是真磨出了洞,就算她们到了盐池,也会羞于见人。她便又翻过身,仰着头,在沙坡上游起泳来。她每一划沙,身子就嗖地下窜一截。沙流进了衣领,弄得身子痒痒地怪舒服。兰兰也开始游泳。沙洼里回响着她们欢乐的叫声。这不期而至的快乐,洗尽了她们的忧虑。
到了沙山下,两人边呸呸地吐溅入口中的沙,边笑成一团。多年了,她们总是活在别人的视线里,从来没这样疯过。不曾想,在这算得上绝境的地方,她们竟一下子拣回了丢失了很久的女儿性。
为庆祝她们的好心情,两人各喝了一口清油。
17
黄昏时分,她们见到了一架驼骨,它立在一个沙漩儿旁。骆驼吃了一惊,倏地一抡脑袋,差点将两人甩下驼背。兰兰很高兴。这是她们在附近看到的跟人最亲近的东西。最扎眼的是头骨,两个黑洞洞的大眼望着来人,它一定茫然许久了。驼骨比较完整,牙齿和肋条也没散架。看得出,骆驼在死前和死后都没遭到野兽的撕扯。看到同类的尸骨,骆驼抡头甩耳了好一阵,时不时就打个响鼻,突突几声。按爹的说法,那是骆驼看到了鬼。鬼最怕唾沫。莫非,死驼的灵魂还守在骨架旁?听说,有种守尸鬼,骨殖几时不入土,它也就一直守着。莹儿不信这大天白日,会有个鬼守着骨架,但还是心里发毛了。
兰兰说,瞧,这是驮盐去的。她指着驼骨旁的碎布屑说,这定然是蒙古人驮盐时累死的驼。莹儿看不出驮盐的迹象,但还是很高兴。毕竟,能发现些啥总是好一些。一路上,除了沙漠、戈壁和沙生植物,很少见到跟人有关的东西。这驼骨至少说明,这儿来过人。
但又想,说不定,这骨架,是野骆驼的呢。怕折了兰兰的兴头,莹儿没说出这话。人在绝境里,是需要盼头的。哪怕它是虚幻的,也比绝望好些。
莹儿想,即使这驼真是去盐池的路上死的,也说明盐池离这儿还远,要是近的话,驼会挣扎着到目的地的。要是再推测驼的死因,她越加心灰了。至少,近处可能没水源,也没嫩草,不然,驼咋会死?瞧那样子,若不是渴死的,便是病死的。死前,它肯定听天由命了。它像坐化的老僧一样坦然。它静静地卧在沙洼里,在命运举了刀抡来时,一副引颈受戮的模样。莹儿长长地叹口气。她想到了自己的命运。
兰兰叫驼卧了,两人又骑了驼。骆驼前仰后俯,晃摇好一阵,才起来了。莹儿回头望望驼骨,说,再见吧,谁叫你也是个苦命呢。想到自己也可能会在前方某处,变成一副骨架,就不由得一阵伤感。
再往前走,虽没明显的路,但遇到的骨头多了,或是骨架,或是腿骨啥的斜插在沙里,很扎眼。莹儿想,看这样子,这儿不是驼道,便是牧场,不然咋会有这么多骨头呢?她轻松了些。
兰兰一直想打个野兔,但怪的是,她们没见到啥活物。兰兰甚至希望再见到豺狗子,虽然一想那瘆虫,仍会心惊肉跳。但要是遇到单个的豺狗子,一枪崩了,也无疑是嘴好肉。可没治,你不想见人家时,人家死皮赖脸地死缠;你想见时,它偏偏连根毛也不送过来。
清油真是好东西,喝一口,热量顶顿饭哩。姑嫂俩就把一口清油当一顿饭。那油不经喝,两人所谓的一口,虽只是一小口,但几顿后,油还是剩少半瓶了。没治。兰兰说定然有饿死鬼跟了,偷她们的油喝。
……终于,发现驼道的迹象了:一具骨架旁,竟有个驮架。这证据,当然很充分了。那驮架上的木头快风化了。旁边,还有不定何年何月屙下的骆驼粪。兰兰兴致很高,不管咋说,总算到正路上了。莹儿当然也高兴,但也有些疑虑,为啥这段路上竟有那么多骨架?既说明了这儿走过好多驮户,也说明经过长途跋涉的驼们,一到这儿,就接近生命极限了。莹儿明白,她们面临的,是跟这沿途的白骨一样可怕的命运。这条路是否真的通向盐池?究竟还有多远?她们的体力能否熬到见到水源?一切的一切,都是未知数。兰兰定然也明白这,她只是不愿意点破而已。
最叫她担心的,却是骆驼。她们有清油提供热量,驼峰却塌成皮囊了。它还能支持多远?毕竟驮两个大活人,少些算,也有二百斤。好几次,它驮着她们起身时,总要摇晃好一阵。上坡时,也老是颤巍巍的,像要摔倒。后来,上坡时,她们就只好下了驼背,拽了驼尾借些力。看来,驼的体能也接近了极限。不然,见到那驼骨时,它咋会受那么大的刺激呢?
18
缓了一阵,两人各喝口清油和水,准备走夜路。驼骨们虽使夜里浸满了阴森,但也在提醒她们路的正确。莹儿想,只要上了路就好,就怕像没头的苍蝇那样瞎撞。兰兰说,不怕慢,就怕站,只要方向对,走一步,就近一步。
她们喊几声:跷!跷!这是叫骆驼卧的命令。
骆驼迟疑了一下,缓慢地卧了。兰兰叹息道,骆驼太累了。两人上了驼,兰兰抖了几次缰绳,喝了几声:嘚!嘚!骆驼晃着身子,想爬起来。它晃了几次,一次好容易撑起了前腿,却又卧下了。它叫了几声,又徒劳地挣扎几次。兰兰说,你先骑,我下来。她下了驼,边喊口令,边扯了驼尾上抬。骆驼长长地叹息一声,卧在那儿,不动了。
莹儿明白它力不从心了,也下了驼。她发现,驼大张着鼻孔,正缓慢而吃力地呼哧着。周围的沙丘上虽有干沙秸,骆驼却不望。莹儿明白,它太渴了,喉咙早成干皮了,它已咽不下那比日头爷还燥的沙秸了。莹儿很感激骆驼,要不是它,她们还不定爬在哪个洼里呢。她想,说啥也不能骑它了,它也不是铁打的身子呀。
兰兰又吆喝几声。驼却只是哀叫,仿佛说,你们走吧,我真的不行了。莹儿听灵官说,骆驼只要有一点儿力气,就会拼了老命,去干自己该干的事。它们是不惜力的。先前的驼队里,走着走着,就有倒毙者。她想,是不是驼骨刺激了它呢?有可能。就像那患了绝症的老人,忽然发现同伴死了。那死,会像鞭子一样抽垮它的意志。莹儿拍拍它的头,说,你怕啥呀?它们是它们,你是你。驼叫了一声,仿佛说,我不是怕,我是实在走不动了。
驼的峰子软成了皮袋,肋条也露了出来。驼吃力地呼吸着,时不时伸出舌头。驼舌上有很厚的苔,颜色或黄或黑。驼的倏然瘫软,虽然与缺养分有关,肯定还有精神原因。莹儿不知道如何才能解除它精神上的疾患。没办法,她既不能瞬息间学会驼语,也不能钻进它的脑子。她想,不管咋说,我们不能扔下它,不仅因为驼值两三千块钱,还因为它已成为她们中的一员。
她忽然明白,为啥这地方有那么多的驼骨。那驼骨,明明在提醒驼们:我们死了,你也该死了。这真是可怕的暗示。驼以为,好多驼都死在这儿,它也一定走不出绝境的。有些驼的体力虽能支持,但那暗示,却一下子摧垮了它们最后的一点儿信念。莹儿想,自己可千万不能学那些死去的驼呀。她想,只要心不死,人是死不了的。
她想,如何救这失去了最后一点信心的驼呢?既然无法钻进它的心中,总得想个别的法子。她想呀想呀,觉得除了给它灌些清油外,也实在没个别的法子。她一说,兰兰拧着眉头解释道,那可是最后一点了,路可能还远呢。莹儿说,我们总不能丢下它,人家已逃了出去,又来找我们……兰兰说成,大不了,我们死在一起。莹儿说,就是,活了,一起活。真要死的话,我们和骆驼一起死。
兰兰取出油瓶,一晃,油就在瓶壁上旋了,旋出很美的纹路。莹儿觉得心叫无形的东西挤压了一下,想来兰兰也这样。这些油,两人还能喝个两三口,虽不多,但这是唯一的食物了。
骆驼贪婪地望那液体,以前她们喝时,它就这样。它当然知道那是美味。以前,清油下来时,主人也会赏些稠油给它。那东西,可不是沙秸。沙秸虽能充饥,但干成麻鞋底的舌头和枯燥成砂纸的食道是无法接受它的。这液体却不然,它滑滑的,带着一抹清凉的神韵。它只能贪婪地望它,望着那两个女人下咽时喉部的蠕动。它甚至能听到那稠亮的甘露滑入食道时发出的咕咕声。干得冒烟的细胞们欢快地叫着,像渴极奔井的羊那样发出咩咩的声音。驼明白自己只能看一看。能看当然不错了,看惯了干燥的沙漠,再看一眼瓶壁上倏然一旋的清凉和润滑,真是痛苦又刺激的事。
它当然想不到那个好看的——虽然她的嘴上也布满了干燥的黑皮——女人会将瓶口伸向它。它以为她在逗自己呢。村里人老这样逗它。人说天窗里吊苜蓿,给老驴种相思病。人们也常给骆驼种诸如此类的相思病。村里娃儿就老举些嫩草引诱它,等得你张口去叼时,他们却倏地拿开了草,发出恶作剧的笑。人都是这样。以前,面对这号捉弄,它总是高傲地闭上眼。但你要知道,此刻,那晕清凉是多大的诱惑呀?哪怕你望它一眼,也是享受呢。
……
那瓶口,竟然伸向它的嘴。它当然感到意外。它当然也知道其中的妙物对两个女人意味着啥。它望望那女人的眼,想捕捉住捉弄它的意蕴。没想到,它看到的,是一双充满了关切的眼。记得,小时候,它一脚踩入鼠洞弄折了腿后,母亲就那样看它。它当然忘不了那眼。你别小看它的记忆,它能记得十多年前某人对它的捉弄,也忘不了八年前某人给过它一把青草。它是最有记性的动物之一。在这一点上,它甚至超过了马。跟马一样,它是公认的能通人性,而且更加厚道。
驼真的被感动了。它毫不怀疑那眼中发出的信息。它明白她是真的想将那清凉给它。它虽然不知道那是仅有的,但早就从两人的举止中明白了它的珍贵——人家都几个时辰喝一小口呢。喝时,她们都闭了眼品味许久,她们当然想叫那味儿印入自己的灵魂深处。当然。
驼当然想不到人家会将瓶口塞进它嘴里,也想不到那滑滑的液体竟会在舌上漫延开来。它听到舌上的味蕾们疯狂地叫着,叫声跟炎阳下的知了那样喧嚣。一股奇异的味道立马渗入了它的灵魂深处。它死也忘不了这味道。这甚至不能算味道了。它成了快乐的旋风,美味的海啸……还有好些比喻,驼死活想不出来了。它觉得舌上的小蕾真是贪婪,它们疯狂地大张了口,跟养熟了的鱼儿乞食时一样。虽然那液体是滑滑的黏黏的,它们还是咂光了好多。驼觉得舌头润泽了许多。它想,这下,又能吃些草了。吃了草,就能接着驮这两个美丽的女人了。
瓶中的液体仍在流着,滑滑的妙物越来越多,舌蕾们吞不及它们了。那清凉又滑向了喉管。喉管欢快地蠕动着,跟它进入母驼产道的阳物一样。因为干燥缺水,那蠕动时的声音像没蜕尽的蛇在游动。对,就是叫响尾蛇的那种。驼想,那喉管,想来裂了好多口子,很像干涸的河床里横七竖八的干口。这一点,是从它吞咽干草时的被剐感觉里推测出的。那地方,本该是滑滑的,有层粘膜呢。现在倒好,成干河床了。它觉得这干渴真是可恶。
驼感到食管在疯狂地扭动着,它当然很快乐。没有比清油进入干裂成山药皮的食管更快乐的事了。它甚至听到了食管快乐的呻吟。那呻吟,很像它第一次深入生驼体内时身不由己地发出的那种。公驼将那些未经驼事的母驼叫生驼。清油比生驼还好。食管也定然这样认为,不然它是不会那样蠕动和呻吟的。你肯定没听过食管的呻吟,那真是天籁。驼虽不知道“大音稀声”这个成语,但还是听懂了食管那无声的啸卷着的大乐。你想,身外是干燥炎热的天空,连空气都在燃烧,身内的那一线清凉和润滑当然会有沁入灵魂深处的穿透力的。驼很感激那女人,她竟将这么好的东西让给她。驼想,要是我是男人的话,我一定会追求她的。但驼也仅仅是想想而已。它的天性告诉它,做梦是个不好的习惯。
清凉又滑向胃部。胃也惊喜地蠕动起来。胃蠕动时真像个怪物,它本该是暗红的,但现在早黑了。不但黑了,而且硬了,跟晒得半干的牛皮一样。不但硬了,而且还收缩了。那模样,跟八十多岁的老妪的脸差不多,跟沙枣树皮差不多,跟挂在屋檐下晒了三天的猪尿泡差不多,跟放在卤水和酱油里煮了五个时辰的胎衣差不多----这么多“差不多”一齐蠕动,当然是怪物了。它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很像三百个老鼠在一起磨牙。胃里顿时弥漫了好多尘埃般的碎屑。它们本来潜伏在胃的皱折处,因为胃液的不辞而别,它们趁机飘了起来,舒活舒活筯骨,活动活动精神。它们也惊喜地发现了顺食管下行的清油。因为胃里还没开窗户呢----这本是豺狗子们的本事—--胃室显得有些暗,尘埃们当然看不到那半透明的东西正姗姗而来。因为沿途的细胞都在趁火打劫,妙物走得很慢,但那味道,还是当了先锋,扑进了它们的鼻子。你可别小看胃,那不是寻常的皮囊,而是一个世界。当然,当它被你弄成腊肉时,那世界就死了,只剩下一块叫你啧啧称赞的僵死。大脑不也一样吗?活着时,它有千般计较,有万种风情,好多缠绵的爱情故事就从其中演绎出来,等它一死,一入你的口,你只会觉得它是绵绵的一团腥,当然也有点香,但你是死活也品不出它曾有过的那么多故事的。胃也是那样。
怪物般的胃的蠕动声很可怕,你是从来没听过那声音的。你可以用世上所有的词汇来形容它,但都显得很惨白。你要是在沙漠渴上三天后,当你气息奄奄魂儿快要飞上半天时,要是看到一晕清凉的湖水时,你也会发出那种声音。但它不是声带发出的,真是出自灵魂。那声音啸卷如天旋风,充斥于九天之外,但很难用音符来再现的。骆驼当然听得见那叫声。它甚至觉得有无数只手伸进胃里,它们也是那声音的制造者。驼很不喜欢那些乱舞的手,它们是一群强盗。它们想将那点儿润滑据为己有,它们叫冲呀杀呀叼呀抢呀。它们发出杂沓的脚步声。驼很为它们羞愧。它心虚地望望举瓶的女人。它很想解释,却想不出该说些啥。
驼体内那些疯狂的大手很快就抢光了进入胃里的稠滑的液体。那形势,像海绵吸水,像春雨灌碱滩,像蝌蚪入鲸口,总之是无声无息又点滴不留。它们意犹未尽地期待更多的来者。驼也一样。但那瓶嘴嗑牙声还是响了。为了使瓶壁上的清油完全滑入驼口,女人摇摇瓶口。驼觉得牙一阵震动。
女人将空瓶扔向沙洼。驼很想告诉女人,那瓶子别扔,因为要是遇上牧人或是驮户们,就可以向他们要些水,这瓶子还能盛水的。它叫了一声。女人当然听不懂那话。驼又想,她是不是嫌我弄脏了瓶口呢?
驼于是忧伤地望望沙洼。它想,随她吧。人家扔的,是人家的东西,管你啥事?
却见另一个女人拣回了瓶子。她用衣襟擦擦瓶嘴,放入挂在它背上的袋里。
19
两人一驼又走向暮色。骆驼虽能起身了,但还不能驮人。这真是雪上加霜的事。骑骆驼虽累,尾骨虽也老叫驼脊骨弄破,总是火烧火燎地疼,腰也老是酸叽叽地难受,但体力的消耗还是比步行小许多。她们喝的那口清油,虽解不了饥渴,但支撑身体的热量,想来还是够的。现在,她们不得不爬那高到天上的沙山。两人毕竟不习惯行沙路,身子也没有“塌膘”,也就是说身上的脂肪还没变成适合走沙路的肌肉。莹儿感到小腿肚子刀割一样。每行走一步,脚都会下陷,而每次下陷,那刀割的感觉都在加剧。脚掌也一样,每走一步,都撕疼一次。撕疼的次数一多,她就浑身瘫软了。
虽也安慰自己:走一步,离目标就会近一步。但每一瞭眼,都是黑黝黝的大沙山。星星虽是照例地低,但星星是星星,她们是她们。对星星,她们已失去了兴趣,早没了初进沙窝时的那份诗意。诗意是一份心情。要是苦难像大山一样砸压下来时,诗意就没了生存的时空。
还是走吧。
拖了刀割般的小腿,望着苍茫暮色里模糊的前路,莹儿胶着了心思,冻结了诗意,木然了心情,守护着希望。她拽着驼尾,但她只是在上坡时才借些力。走在平处时,她尽量快些挪那灌了铅的双腿,不使自己成了驼的累赘。
兰兰右手拽了骆驼笼头,表面看她在吆驼,其实也在借力。莹儿拽了驼尾,在沙上行走。你只要稍稍借点力,行来就会轻松许多。要知道,两人虽都在借驼力,但相较于骑,已给骆驼节省了大量的体力。
虽然行走时的腿疼跟刀割一样,莹儿还是时不时闭了眼。她困极了。要不是时有沙绊她一下,她会睡熟的。没办法。那困,是窖里的酒,越窖,酒味儿就越浓。某个瞬间,她甚至觉得自己已睡在床上,就松开了手,睡在沙上了。幸好,兰兰在牵驼拐过沙湾时回首望了一下。兰兰说,幸好没风,要不然,就再也找不到你了。风不但会吹去沙上的所有印迹,还会发出许多怪怪的声音。它既能卷走兰兰喊莹儿的声音,还会营造出其他声音来引诱莹儿。莹儿会以为那声音是兰兰发出的,就会一直跟了那声音,走到一个兰兰再也找不到的地方。
好多困死在沙漠里的人就是这样死的。
为防止莹儿再次睡着。兰兰取了一根绳子,一头拴在莹儿腰上,一头系在驮架上。兰兰稍将绳子放长些,要是莹儿拽着驼尾时,绳子是松的。一旦她松了驼尾,绳子就一下子扯紧了,用另一手拽着绳子的兰兰就会停下,叫醒可能再次倒在沙上的莹儿。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兰兰必须吆好骆驼,否则的话,驼一惊,绳子就可能一下子扯倒莹儿。其情形,跟摔下马背脚却没脱出马镫的骑手一样,一些骑手就这样被摔成了稀巴烂。为了预防类似的危险,兰兰将拴在驮架上的绳子那头绾成了抽蹄扣,万一有了意外,她一抽,绳子就脱了驮架。
姑嫂俩就这样半眯半醒地在沙山间颠簸着。进沙窝时尚有驼铃,但在逃豺狗子时丢了,路上就只有沙沙声了。时不时还能听到驼打个响鼻,那声音很像炸雷,总能惊醒时不时就迷糊的莹儿。
手电里的电不多了,虽然她们节省着用,但坐吃都能山空的。只有在探路时,兰兰才舍得打亮手电。有时,那光柱就照出一具狰狞的骨架。要是在以前,她们都会吱哇乱叫,但现在,早就习惯了它们。要是许久不见它们,兰兰心里还会嘀咕,害怕又走错了路。那些骨架,也不全是骆驼的,有时,还能看到很像狗的,但她们分不清那是狗还是狐子。按说,流动的沙会埋了那些骨架,可怪的是偏偏没有,也许是北面的沙山挡住了大风的缘故。
约到半夜时分,两人实在走不动了,就缓了一阵。才停下,莹儿便堕入梦乡。兰兰怕自己睡着,不敢坐下。她明白要是夜里不多赶些路,白天会叫晒成干尸。但实在太渴了,塑料拉子里也只剩下一点儿水了,至多有三五口。这真是要命的事。所以,那渴虽变成了火焰在烤喉咙烤心,却不敢打水的主意。兰兰想,这点儿水,就用来救命吧,要是一人叫太阳晒得昏死过去,另一人就用它来救对方的命。别小看那点儿水,有时,几滴水也能推迟已经降临的死亡呢。
困意很强大,像黑夜和死亡一样不可抗拒,兰兰就倚着骆驼眯了眯。她没叫骆驼卧,因为只要它一卧,自己也会身不由己地堕进梦里……不,不是梦里,她已没气力做梦了。她就倚着骆驼立在那儿。她想,无论骆驼是走还是卧,只要它一动,自己就会醒来。
随后,她闭了眼。她觉得向一团巨大的黑里堕去。
版权声明
为加强原创内容保护,日前,甘肃日报、甘肃日报报业集团各子报、甘肃新媒体集团各平台已将其所有的版权统一授予甘肃媒体版权保护中心进行保护、维权及给第三方的授权许可。即日起,上述媒体采访、拍摄、编辑、制作并刊登的,包括文字、图片、摄影、视频、音频等原创作品,文创产品、文艺作品,以及H5、海报、AR、VR、手绘、沙画、图解等新媒体产品,任何机构、媒体及自媒体未经甘肃媒体版权保护中心许可,不得转载、修改、摘编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并传播上述作品。
如需使用相关内容,请致电0931-8159799。
甘肃媒体版权保护中心
相关新闻
- 2020年08月26日【名家·文学·牛庆国·代表作】诗篇